Scalable Diffusion Models with Transformers

Scalable Diffusion Models with Transformers | ICCV 2023
Bayes’ Theorem | Bayesian Inference
贝叶斯公式(Bayes’ Theorem)是概率论中的基本定理,描述了如何根据新证据更新对事件概率的信念。它是贝叶斯统计学、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一种系统化的方法来处理不确定性和进行推理。
$$P(A|B) = \frac{P(B|A) \times P(A)}{P(B)}$$
$$P(\theta|D) = \frac{P(D|\theta) \times P(\theta)}{P(D)}$$
或写成:
$$\text{后验概率} = \frac{\text{似然} \times \text{先验}}{\text{证据}}$$
| 符号 | 名称 | 含义 |
|---|---|---|
| $P(\theta|D)$ | 后验概率 | 看到数据 $D$ 后,参数 $\theta$ 的概率 |
| $P(D|\theta)$ | 似然 | 给定参数 $\theta$,观测到数据 $D$ 的概率 |
| $P(\theta)$ | 先验概率 | 看到数据前,对参数 $\theta$ 的初始信念 |
| $P(D)$ | 边缘似然/证据 | 数据 $D$ 出现的总概率(归一化常数) |
$$P(D) = \int P(D|\theta)P(\theta)d\theta$$
或离散情况:
$$P(D) = \sum_{\theta} P(D|\theta)P(\theta)$$
贝叶斯公式回答:**”看到证据后,我应该如何更新我的信念?”**
$$\text{新信念} = \frac{\text{旧信念} \times \text{证据支持度}}{\text{归一化}}$$
核心思想:
场景:
问:你真的患病的概率是多少?
解答:
设:
已知:
计算边缘似然:
$$P(B) = P(B|A)P(A) + P(B|\neg A)P(\neg A)$$
$$= 0.95 \times 0.01 + 0.05 \times 0.99 = 0.059$$
应用贝叶斯公式:
$$P(A|B) = \frac{P(B|A) \times P(A)}{P(B)} = \frac{0.95 \times 0.01}{0.059} \approx 0.16$$
结论:即使测试阳性,患病概率只有 **16%**!
反直觉原因:先验概率很低(1%),大部分阳性结果来自假阳性。
场景:
问:含”中奖”的邮件是垃圾邮件的概率?
解答:
设:
已知:
计算:
$$P(W) = 0.8 \times 0.3 + 0.05 \times 0.7 = 0.275$$
$$P(S|W) = \frac{0.8 \times 0.3}{0.275} \approx 0.87$$
结论:含”中奖”的邮件有 87% 概率是垃圾邮件。
场景:训练一个分类模型
目标:找到最优参数 $\theta$
$$P(\theta|D) = \frac{P(D|\theta) \times P(\theta)}{P(D)}$$
最大后验估计(MAP):
$$\theta_{MAP} = \arg\max_{\theta} P(\theta|D) = \arg\max_{\theta} P(D|\theta)P(\theta)$$
根据领域知识或假设选择先验分布:
$$P(\theta)$$
常见先验:
观测数据 $D = {x_1, x_2, \ldots, x_N}$
根据模型计算数据的似然:
$$P(D|\theta) = \prod_{i=1}^{N} P(x_i|\theta)$$
计算后验分布:
$$P(\theta|D) = \frac{P(D|\theta)P(\theta)}{P(D)}$$
| 方面 | 贝叶斯学派 | 频率学派 |
|---|---|---|
| 参数性质 | 随机变量(有分布) | 固定未知值 |
| 概率含义 | 信念程度 | 长期频率 |
| 推断方法 | 后验分布 | 点估计 + 置信区间 |
| 先验知识 | 必须指定先验 | 不使用先验 |
| 不确定性 | 参数的概率分布 | 估计的抽样分布 |
| 小样本 | 可利用先验 | 可能不稳定 |
问题:抛硬币 10 次,8 次正面,估计正面概率 $\theta$
频率学派:
$$\hat{\theta}_{MLE} = \frac{8}{10} = 0.8$$
贝叶斯学派(假设先验 $\theta \sim \text{Beta}(2,2)$):
$$P(\theta|D) = \text{Beta}(2+8, 2+2) = \text{Beta}(10, 4)$$
后验均值:
$$\mathbb{E}[\theta|D] = \frac{10}{10+4} \approx 0.71$$
差异:贝叶斯方法考虑了先验信念(硬币应该接近公平),结果更保守。
$$P(y|x_1, \ldots, x_n) = \frac{P(y) \prod_{i=1}^{n} P(x_i|y)}{P(x_1, \ldots, x_n)}$$
应用:文本分类、垃圾邮件过滤
$$P(w|D) = \frac{P(D|w)P(w)}{P(D)}$$
优势:提供预测的不确定性
对网络权重建模为分布而非点估计:
$$P(w|D) \propto P(D|w)P(w)$$
应用:不确定性量化、主动学习
当后验 $P(\theta|D)$ 难以计算时,用简单分布 $q(\theta)$ 近似:
$$\min_q D_{KL}(q(\theta)||P(\theta|D))$$
应用:VAE、主题模型(LDA)
通过采样近似后验分布:
$$\theta^{(t+1)} \sim P(\theta|D)$$
应用:贝叶斯深度学习、概率编程
目的:表达”无知”
例子:
定义:后验与先验同分布族
例子:
| 似然 | 共轭先验 | 后验 |
|---|---|---|
| 伯努利 | Beta | Beta |
| 正态(已知方差) | 正态 | 正态 |
| 泊松 | Gamma | Gamma |
| 多项式 | Dirichlet | Dirichlet |
优势:后验有闭式解,计算简单
目的:防止过拟合
例子:
从数据中估计先验的超参数:
$$\hat{\alpha} = \arg\max_{\alpha} P(D|\alpha)$$
回答:
回答:
回答:
回答:可以!这是贝叶斯方法的优势。
顺序更新:
$$P(\theta|D_1, D_2) = \frac{P(D_2|\theta)P(\theta|D_1)}{P(D_2|D_1)}$$
前一次的后验成为下一次的先验:
1 | 先验 → [数据1] → 后验1 → [数据2] → 后验2 → ... |
1 | # 弱信息先验(数据主导) |
1 | # 先验预测检查 |
1 | # 后验预测检查 |
1 | # 避免数值下溢 |
1 | import torch |
Variational Inference | Evidence Lower Bound | VAE Paper
ELBO(Evidence Lower Bound,证据下界)是变分推断中的核心概念,用于近似难以计算的边缘似然 $\log p(x)$。ELBO 提供了一个可优化的目标函数,使得复杂概率模型的训练变得可行,是现代深度生成模型(如 VAE)的理论基础。
ELBO 是对数边缘似然 $\log p(x)$ 的下界:
$$\text{ELBO} = \mathbb{E}{q(z|x)}[\log p(x,z)] - \mathbb{E}{q(z|x)}[\log q(z|x)]$$
或等价形式:
$$\text{ELBO} = \mathbb{E}{q(z|x)}[\log p(x|z)] - D{KL}(q(z|x)||p(z))$$
其中:
目标:最大化边缘似然 $\log p(x)$
$$\log p(x) = \log \int p(x,z)dz$$
这个积分通常难以计算。引入变分分布 $q(z|x)$:
$$\begin{align}
\log p(x) &= \log \int p(x,z)dz \
&= \log \int \frac{q(z|x)}{q(z|x)} p(x,z)dz \
&= \log \mathbb{E}{q(z|x)}\left[\frac{p(x,z)}{q(z|x)}\right] \
&\geq \mathbb{E}{q(z|x)}\left[\log\frac{p(x,z)}{q(z|x)}\right] \quad \text{[Jensen 不等式]} \
&= \text{ELBO}
\end{align}$$
关键关系:
$$\log p(x) = \text{ELBO} + D_{KL}(q(z|x)||p(z|x))$$
由于 $D_{KL} \geq 0$,所以 ELBO 是 $\log p(x)$ 的下界。
解释 1:重构 + 正则化
$$\text{ELBO} = \underbrace{\mathbb{E}{q(z|x)}[\log p(x|z)]}{\text{重构项}} - \underbrace{D_{KL}(q(z|x)||p(z))}_{\text{正则化项}}$$
解释 2:似然 - 复杂度
$$\text{ELBO} = \underbrace{\mathbb{E}{q(z|x)}[\log p(x|z)]}{\text{数据似然}} - \underbrace{D_{KL}(q(z|x)||p(z))}_{\text{模型复杂度惩罚}}$$
这体现了奥卡姆剃刀原则:在解释数据的同时保持模型简单。
真实后验 $p(z|x) = \frac{p(x|z)p(z)}{p(x)}$ 难以计算,因为:
$$p(x) = \int p(x|z)p(z)dz$$
这个积分在高维空间中通常没有闭式解。
最大化 ELBO 等价于最小化 $D_{KL}(q(z|x)||p(z|x))$:
$$\begin{align}
\log p(x) &= \text{ELBO} + D_{KL}(q(z|x)||p(z|x)) \
\max_q \text{ELBO} &\Leftrightarrow \min_q D_{KL}(q(z|x)||p(z|x))
\end{align}$$
因为 $\log p(x)$ 不依赖于 $q$,最大化 ELBO 就是让 $q(z|x)$ 尽可能接近真实后验 $p(z|x)$。
ELBO 可以通过蒙特卡洛采样估计:
$$\text{ELBO} \approx \frac{1}{L}\sum_{i=1}^{L} \log p(x|z_i) - D_{KL}(q(z|x)||p(z))$$
其中 $z_i \sim q(z|x)$。
1 | 输入 x → Encoder → μ(x), σ(x) → 采样 z ~ N(μ,σ²) → Decoder → 重构 x̂ |
$$\text{ELBO} = \mathbb{E}{q(z|x)}[\log p(x|z)] - D{KL}(q(z|x)||p(z))$$
重构项(需要采样估计):
$$\mathbb{E}{q(z|x)}[\log p(x|z)] \approx \frac{1}{L}\sum{i=1}^{L} \log p(x|z_i), \quad z_i \sim q(z|x)$$
通常 $L=1$(单样本估计)。对于伯努利分布的似然,这等价于二元交叉熵。
KL 项(有闭式解):
$$D_{KL}(q(z|x)||p(z)) = -\frac{1}{2}\sum_{j=1}^{J}\left(1 + \log\sigma_j^2 - \mu_j^2 - \sigma_j^2\right)$$
其中 $J$ 是隐变量维度。
VAE 的损失函数是 负 ELBO(因为要最小化):
$$\mathcal{L} = -\text{ELBO} = \underbrace{-\mathbb{E}{q(z|x)}[\log p(x|z)]}{\text{重构损失}} + \underbrace{D_{KL}(q(z|x)||p(z))}_{\text{KL 损失}}$$
直接从 $z \sim \mathcal{N}(\mu(x), \sigma^2(x))$ 采样不可微,无法反向传播。
核心思想:将随机性外部化
1 | 原始:z ~ N(μ, σ²) ❌ 不可微 |
1 | 损失 → Decoder → z = μ + σε → μ, σ → Encoder |
1 | import torch |
正则化是防止模型过拟合的技术,通过约束模型复杂度:
$$\text{损失函数} = \text{数据拟合项} + \lambda \times \text{正则化项}$$
常见类型:
ELBO 天然包含正则化:
$$\text{ELBO} = \underbrace{\mathbb{E}[\log p(x|z)]}{\text{拟合数据}} - \underbrace{D{KL}(q(z|x)||p(z))}_{\text{正则化}}$$
KL 散度项的作用:
如果只优化重构损失:
1 | loss = reconstruction_loss # 没有 KL 项 |
问题:
KL 正则化的效果:
用途:生成模型、表示学习
1 | # 训练后生成新样本 |
用途:文档主题发现
用途:不确定性量化
用途:序列建模
用途:聚类分析
有时需要调整 KL 项的权重:
1 | loss = reconstruction_loss + beta * kl_loss # β-VAE |
训练初期降低 KL 权重,逐渐增加:
1 | beta = min(1.0, epoch / warmup_epochs) |
原因:避免”后验坍缩”(posterior collapse),即 $q(z|x)$ 过早收敛到先验。
为每个隐变量维度设置最小 KL 值:
1 | kl_per_dim = kl_loss / latent_dim |
作用:防止某些维度被忽略。
1 | # 使用 log(σ²) 而非 σ |
解答:根据 Jensen 不等式,对于凹函数 $\log$:
$$\log \mathbb{E}[X] \geq \mathbb{E}[\log X]$$
因此:
$$\log p(x) = \log \mathbb{E}{q(z|x)}\left[\frac{p(x,z)}{q(z|x)}\right] \geq \mathbb{E}{q(z|x)}\left[\log\frac{p(x,z)}{q(z|x)}\right] = \text{ELBO}$$
解答:在贝叶斯推断中,$p(x)$ 被称为”证据”(evidence)或”边缘似然”(marginal likelihood),因为它是观测数据 $x$ 的概率。ELBO 是这个证据的下界。
解答:重参数化将随机性从参数中分离出来:
1 | z = μ(x; θ) + σ(x; θ) ⊙ ε, ε ~ N(0,I) |
原因:
改进方法:
Information Theory | Kullback-Leibler Divergence
KL 散度(Kullback-Leibler Divergence),也称为相对熵(Relative Entropy),是信息论和统计学中用于衡量两个概率分布差异的重要度量。它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变分推断等领域有广泛应用。
本笔记重点介绍 KL 散度的基础定义、数学推导、核心性质以及其在机器学习中的意义。
对于离散概率分布 $P$ 和 $Q$,KL 散度定义为:
$$D_{KL}(P||Q) = \sum_{x} P(x) \log\frac{P(x)}{Q(x)}$$
对于连续概率分布,KL 散度定义为:
$$D_{KL}(P||Q) = \int p(x) \log\frac{p(x)}{q(x)} dx$$
其中:
$$D_{KL}(P||Q) \geq 0$$
当��仅当 $P = Q$ 时,等号成立(即 $D_{KL}(P||Q) = 0$)。
$$D_{KL}(P||Q) \neq D_{KL}(Q||P)$$
这意味着 KL 散度不是真正的距离度量,因为它不满足对称性。
KL 散度不满足三角不等式:
$$D_{KL}(P||R) \not\leq D_{KL}(P||Q) + D_{KL}(Q||R)$$
因此,KL 散度不是度量空间中的距离函数。
KL 散度关于第一个参数 $P$ 是凸函数。
KL 散度表示:用分布 $Q$ 来编码分布 $P$ 的样本时,相比用 $P$ 自身编码所需的额外信息量(以比特或 nats 为单位)。
KL 散度衡量分布 $Q$ 对分布 $P$ 的近似程度:
在机器学习中,通常:
分布 $P$ 的信息熵定义为:
$$H(P) = -\sum_{x} P(x) \log P(x)$$
它表示编码分布 $P$ 的样本所需的平均最小比特数。
用分布 $Q$ 来编码分布 $P$ 的样本所需的平均比特数:
$$H(P, Q) = -\sum_{x} P(x) \log Q(x)$$
$$\begin{align}
D_{KL}(P||Q) &= H(P, Q) - H(P) \
&= -\sum_{x} P(x) \log Q(x) + \sum_{x} P(x) \log P(x) \
&= \sum_{x} P(x) [\log P(x) - \log Q(x)] \
&= \sum_{x} P(x) \log\frac{P(x)}{Q(x)}
\end{align}$$
这表明 KL 散度是使用次优编码方案 $Q$ 相比最优编码方案 $P$ 所需的额外信息量。
我们使用 Jensen 不等式来证明 KL 散度的非负性。
对于凸函数 $f(x)$ 和概率分布 $P$:
$$f\left(\sum_{x} P(x) \cdot x\right) \leq \sum_{x} P(x) \cdot f(x)$$
对于凹函数(如 $\log$),不等号反向。
由于 $f(x) = -\log(x)$ 是凸函数,我们有:
$$\begin{align}
D_{KL}(P||Q) &= \sum_{x} P(x) \log\frac{P(x)}{Q(x)} \
&= -\sum_{x} P(x) \log\frac{Q(x)}{P(x)} \
&\geq -\log\left(\sum_{x} P(x) \cdot \frac{Q(x)}{P(x)}\right) \quad \text{[Jensen 不等式]} \
&= -\log\left(\sum_{x} Q(x)\right) \
&= -\log(1) \
&= 0
\end{align}$$
等号成立当且仅当 $\frac{Q(x)}{P(x)}$ 为常数,即 $P(x) = Q(x)$ 对所有 $x$ 成立。
结论:$D_{KL}(P||Q) \geq 0$,且仅当 $P = Q$ 时等号成立。
在机器学习中,我们通常希望找到参数 $\theta$ 使得模型分布 $P_\theta$ 尽可能接近真实数据分布 $P_{data}$。
$$\begin{align}
\min_\theta D_{KL}(P_{data}||P_\theta) &= \min_\theta \sum_{x} P_{data}(x) \log\frac{P_{data}(x)}{P_\theta(x)} \
&= \min_\theta \left[\sum_{x} P_{data}(x) \log P_{data}(x) - \sum_{x} P_{data}(x) \log P_\theta(x)\right] \
&= \min_\theta \left[-\sum_{x} P_{data}(x) \log P_\theta(x)\right] \quad \text{[第一项与 $\theta$ 无关]} \
&= \max_\theta \sum_{x} P_{data}(x) \log P_\theta(x)
\end{align}$$
在实践中,我们无法直接访问 $P_{data}$,但可以从数据集 ${x_1, x_2, \ldots, x_N}$ 中采样。使用经验分布:
$$P_{data}(x) \approx \frac{1}{N} \sum_{i=1}^{N} \delta(x - x_i)$$
代入上式:
$$\max_\theta \sum_{x} P_{data}(x) \log P_\theta(x) \approx \max_\theta \frac{1}{N} \sum_{i=1}^{N} \log P_\theta(x_i)$$
这正是最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的目标函数!
结论:最小化 KL 散度等价于最大化似然函数。
假设真实分布 $P = [0.5, 0.3, 0.2]$,近似分布 $Q = [0.4, 0.4, 0.2]$。
计算 $D_{KL}(P||Q)$:
$$\begin{align}
D_{KL}(P||Q) &= 0.5 \cdot \log\frac{0.5}{0.4} + 0.3 \cdot \log\frac{0.3}{0.4} + 0.2 \cdot \log\frac{0.2}{0.2} \
&= 0.5 \cdot \log(1.25) + 0.3 \cdot \log(0.75) + 0.2 \cdot \log(1) \
&= 0.5 \times 0.2231 + 0.3 \times (-0.2877) + 0 \
&= 0.1116 - 0.0863 \
&\approx 0.0253 \text{ nats}
\end{align}$$
转换为 bits(除以 $\ln 2 \approx 0.693$):
$$D_{KL}(P||Q) \approx 0.0365 \text{ bits}$$
对于两个一维高斯分布:
KL 散度的闭式解为:
$$D_{KL}(P||Q) = \log\frac{\sigma_2}{\sigma_1} + \frac{\sigma_1^2 + (\mu_1 - \mu_2)^2}{2\sigma_2^2} - \frac{1}{2}$$
特殊情况:当 $Q = \mathcal{N}(0, 1)$(标准正态分布)时:
$$D_{KL}(P||Q) = \frac{1}{2}\left(\mu_1^2 + \sigma_1^2 - \log\sigma_1^2 - 1\right)$$
这个公式在 VAE(变分自编码器)中被广泛使用。
在贝叶斯推断中,我们希望计算后验分布 $P(\theta|X)$,但通常难以直接计算。变分推断使用一个简单的分布 $Q(\theta)$ 来近似:
$$\min_Q D_{KL}(Q(\theta)||P(\theta|X))$$
VAE 的损失函数包含 KL 散度项,用于正则化潜在空间:
$$\mathcal{L} = \mathbb{E}{q(z|x)}[\log p(x|z)] - D{KL}(q(z|x)||p(z))$$
其中:
在强化学习中,KL 散度用于约束策略更新的幅度:
$$\max_\theta \mathbb{E}{\pi_\theta}[R] \quad \text{s.t.} \quad D{KL}(\pi_{old}||\pi_\theta) \leq \delta$$
这是 TRPO(Trust Region Policy Optimization)和 PPO(Proximal Policy Optimization)的核心思想。
使用 KL 散度让小模型(学生)学习大模型(教师)的输出分布:
$$\mathcal{L} = D_{KL}(P_{teacher}||P_{student})$$
虽然 GAN 不直接优化 KL 散度,但理论分析表明,GAN 的目标函数与 JS 散度(Jensen-Shannon Divergence)相关,而 JS 散度是基于 KL 散度定义的:
$$D_{JS}(P||Q) = \frac{1}{2}D_{KL}(P||M) + \frac{1}{2}D_{KL}(Q||M)$$
其中 $M = \frac{1}{2}(P + Q)$。
| 特性 | 前向 KL $D_{KL}(P||Q)$ | 反向 KL $D_{KL}(Q||P)$ |
|---|---|---|
| 优化目标 | 最大似然估计 | 变分推断 |
| 行为 | Zero-avoiding(避免零概率) | Zero-forcing(强制零概率) |
| 多模态处理 | 覆盖所有模式(分散) | 选择单一模式(集中) |
| 应用 | 监督学习、MLE | VAE、变分推断 |
JS 散度是 KL 散度的对称化版本:
$$D_{JS}(P||Q) = \frac{1}{2}D_{KL}(P||M) + \frac{1}{2}D_{KL}(Q||M)$$
其中 $M = \frac{1}{2}(P + Q)$。
性质:
Wasserstein 距离(也称为 Earth Mover’s Distance)是另一种衡量分布差异的度量,在 GAN 中被广泛使用(WGAN)。
与 KL 散度相比:
$$D_{\chi^2}(P||Q) = \sum_{x} \frac{(P(x) - Q(x))^2}{Q(x)}$$
与 KL 散度相比,$\chi^2$ 散度对分布差异更敏感。
原因:KL 散度的定义中,$P$ 和 $Q$ 的角色不同:
$$D_{KL}(P||Q) = \sum_{x} P(x) \log\frac{P(x)}{Q(x)}$$
交换 $P$ 和 $Q$ 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直观理解:
**前向 KL $D_{KL}(P||Q)$**:
不可以。根据 Gibbs 不等式,KL 散度始终非负:
$$D_{KL}(P||Q) \geq 0$$
当且仅当 $P = Q$ 时,$D_{KL}(P||Q) = 0$。
当 $P(x) > 0$ 但 $Q(x) = 0$ 时,$\log\frac{P(x)}{Q(x)} = \infty$,导致 KL 散度为无穷大。
解决方法:
1 | # 不稳定的实现 |
1 | # 添加小的 epsilon 避免 log(0) |
1 | # PyTorch |
Skills(技能) 是扩展 Claude Code 能力的自定义工作流。通过 Markdown 文件定义,可以用斜杠命令调用或自动加载。
Skills 遵循开放的 Agent Skills 标准,可跨多个 AI 工具使用。
/commit、/review)1 | skill-name/ |
| 位置 | 路径 | 作用域 |
|---|---|---|
| 个人级 | ~/.claude/skills/<skill-name>/SKILL.md |
用户所有项目 |
| 项目级 | .claude/skills/<skill-name>/SKILL.md |
仅当前项目 |
| 企业级 | 通过设置管理 | 组织范围 |
优先级:项目级 > 个人级 > 企业级
最简单的 skill 只需一个带 YAML 头的 SKILL.md 文件:
1 |
|
| 字段 | 类型 | 说明 |
|---|---|---|
name |
string | 显示名称(成为 /斜杠命令) |
description |
string | 功能描述 - 用于自动调用判断 |
disable-model-invocation |
boolean | 为 true 时仅用户可调用(禁止自动加载) |
user-invocable |
boolean | 为 false 时仅 Claude 可调用(菜单中隐藏) |
allowed-tools |
array | Claude 可使用的工具列表(无需权限提示) |
context |
string | 设为 fork 在隔离的子代理中运行 |
agent |
string | 指定代理类型(如 Explore、Plan) |
argument-hint |
string | 自动补全提示(如 [issue-number]) |
用户显式使用斜杠命令:
1 | /skill-name |
当用户请求匹配 skill 的 description 时,Claude 自动加载:
1 | 用户:"这个认证流程是如何工作的?" |
控制自动调用:
disable-model-invocation: true 禁止自动加载$ARGUMENTS 占位符捕获所有参数为单个字符串:
1 |
|
用法:/fix-issue 123 → “修复 GitHub issue 123…”
用 $0、$1、$2 等访问单个参数:
1 |
|
用法:/migrate-component SearchBar React Vue
$0 = SearchBar$1 = React$2 = Vue使用反引号`和 ! 在 skill 运行前执行 shell 命令:
1 |
|
在隔离上下文中运行 skill,避免污染主对话:
1 |
|
限制 Claude 在 skill 中可使用的工具:
1 |
|
fix-issue、explain-code1 |
|
1 |
|
问题:Claude 没有在预期时加载你的 skill。
解决方案:
description 更具体,包含用户会自然说出的关键词/context 确保 skill 描述未超出字符预算问题:Skill 在不需要时加载。
解决方案:
disable-model-invocation: true 要求显式调用问题:$ARGUMENTS 或 $0、$1 未被替换。
解决方案:
/skill-name arg1 arg21 |
|
1 |
|
/ 命令显示所有可用 skills 并支持自动补全context: fork 保持主上下文清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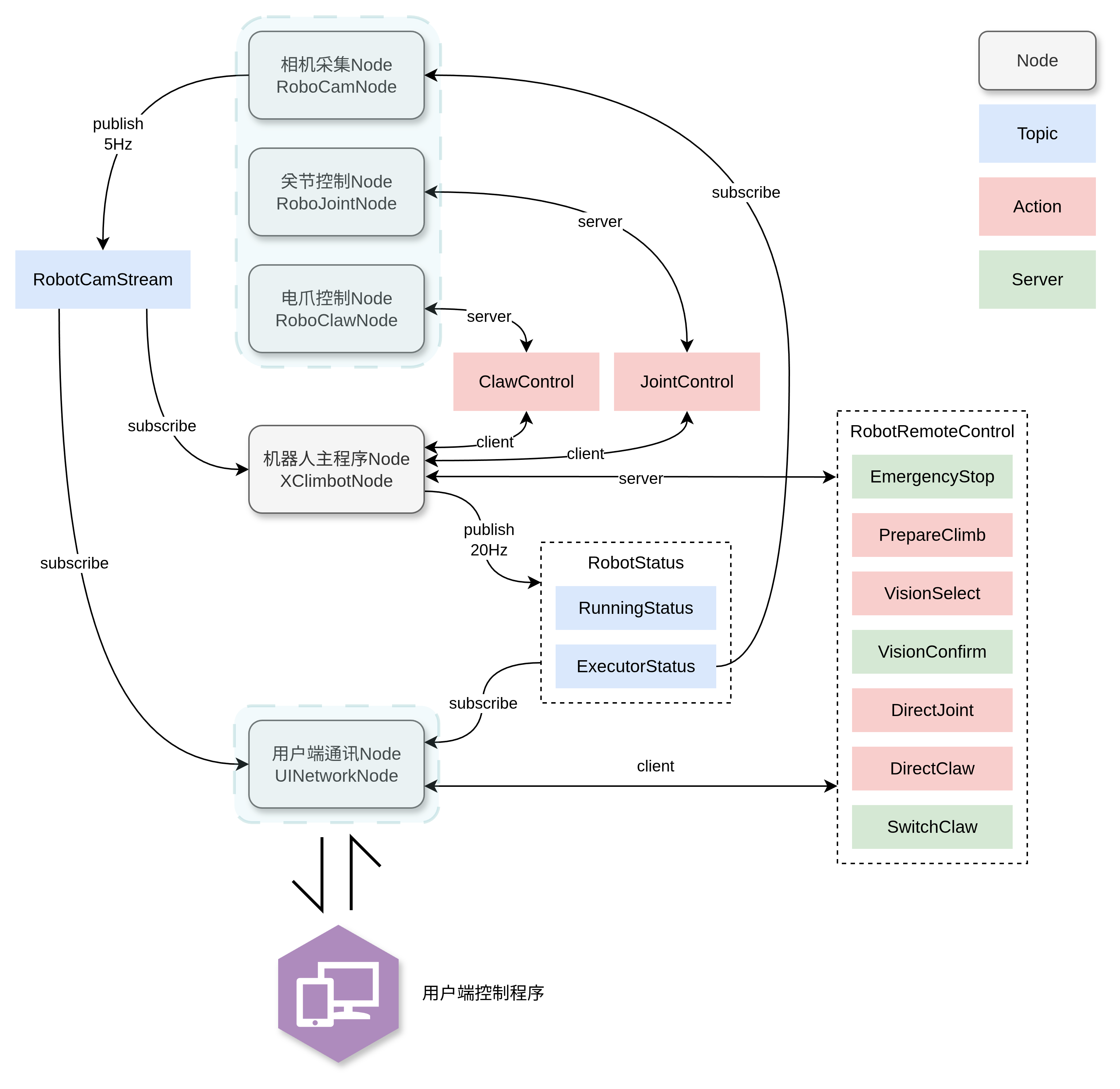
待定,与上塔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