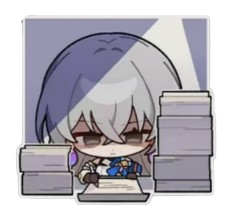tzc转发的小红书推荐了这本书,推荐语:
做过很多爱,爱过很多人,被很多人爱过,才能写出这样的小书。
书很短,大概一给小时不到就能读完。但其实我读了一个半小时,主要是因为群友们在批判马提尼女士在恋爱中的🐢🐢行为,比较刺激所以时不时开小差看消息(对不起我紫菜)。
看完之后,无论是对书中的主人公还是马提尼女士,我都觉得她们在浪漫关系中能有此激情我真的很羡慕,我不希望她的这种激情被“利益分析”,“思考对方爱不爱自己”,过分影响。有的时候,浪漫关系,激情本身的存在,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浪漫和激情不存在对错,只要自己能够承受,没有超过自己的度,那就没必要被批判。在我听来,分析对象是否爱自己(甚至是通过给自己花了多少钱的方式。。?),自己的爱是否值得,只不过是为了遮掩自己激情褪去的不堪。
于是晚上给马提尼分享了《简单的激情》。
爱欲就像海潮,涌起消退,重要的或许不是人,而是那种情愫,爱在某种程度上会物化别人,所以才需要提出“爱具体的人”,但是具体的人又岂是这么好爱的?情欲说到底还是一件自己的浪漫事。
是的,我在还没读完p10和p11的同时,开了p12的坑
这里摘写若干我认为有价值的原文或者书评
“纯粹之爱”
韩教授全文诉说的“爱欲”的最高形态被称作“纯粹之爱”,在这里他并没有直接做定义,我们则从斯滕伯格的爱情三元素理论开始理解即纯粹之爱需要包括激情、亲密和承诺才能构成“爱”的理性与感性并存。
爱情既包括感性的甜蜜纵容,又有着理性的升华包容;既有着肉欲的激情冲动,还含有灵魂的契合相融。互相保有自主的空间,却也有着舒适的亲密感。相互信任并且互相理解。同时具有着“缘分”,这个缘分既能保证相遇,又能保证不分离。“爱欲”
它包含在纯粹之爱之中也就是说是一种“爱的原发状态”,一种不完满的“爱”,它是主体在产生对性状的自我意识之后具备的“知性”(Verstand)能力,即能够综合分析判断“情”和“欲”的范畴,将这两个经验表象通过范畴结成的大网捕捉到自我之中形成观念。
“情感”
顾名思义这是爱的经验,是自我与他者之间产生的“情愫”,是“爱欲”被充实的质料。
“性”
这是一种主观的体验,也就是说它是在进行性行为之后的一种“体验”。
这四者之间的关系
纯粹之爱—超验(理性),爱欲(性欲)-先验(知性),情感(激情)-经验(感性),性体验(性满足)-后验(经验)
韩教授开篇便提出了“导致爱情危机的不仅仅是对他者的选择增多,也是他者本身的消亡……伴随着个体的‘自恋‘情节的加深。”这一直接观点,一针见血刺疼了时代的根源,当然我们还要区分“自恋”与“自爱”这对范畴。“自恋(Narzissmus)与自爱(Eigenliebe)不同。自爱的主体以自我为出发点,与他者明确划清界限;自恋的主体界限是模糊的整个世界只是自我的一个倒影。”也就是说自爱的人能够清晰的界定主体与客体(这个客体是具有自由意志的)、自我与他者,并且其认识标准和世界观是多元性的,此时他者对于自我而言是具有“意义”的。而“自恋”的人对于主客体之间没有能动的区分能力,无法认识到他者身上的差异性,在对于时空中的存在只是“自我”的缩影,即他者此时只是自我的强行解释。
在这里我们要明确的是,每个人在追求他者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的产出“愿望”,愿望不可避免,但其形式与质料必然存在差异。我们无需担心缺乏信息的“选择自由”会面临着“愿望的终结”,恰恰相反,因为愿望是相对于他者而言的愿望,“被剥夺的否定性滋养着愿望”。信息过多会导致他者无法被“理想化”,信息的缺失恰恰能缔造他者的存在,因为信息是肯定性的,而他者的塑造确是否定性的。“色情片就是通过将视觉信息无限倍地扩大来毁掉人们对情欲的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接受了大量色情产物后面对真实的性行为时便不会得到健康完整的“性满足”,即齐泽克讨论的“快感”。
受爱欲驱使的灵魂能够创造出具有普遍价值的美的事物和行为。爱欲并非普遍认为的那样与感官和快乐对立。只是因为今天的爱情被世俗化为性爱,爱欲才逐渐远离了它们。”世俗化的爱情不再具备古希腊人所憧憬的美好品质——勇敢、激情,理性。而爱欲与生活甚至是政治息息相关,这也就引导我们来到了第六章的标题——爱欲政治学。缺乏这些品质的爱欲堕落成为了单向度的欲望,也就是对色情的向往。色情升级了自我的自恋倾向,使自我丧失了完成“爱情双人舞”的能力,因为自恋的自我拒绝与他者的融合甚至放弃认识他者。失去了对爱欲的追求,也就引伸联系到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创新和革命的源泉。韩炳哲教授在本章的最后说到:“表达出来的爱欲,代表着对其他个体生命形式和社群组织的革命性渴望。是的,它维护着人们对未来的忠诚。”
从书中全文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出,从历史传统中就出现定义的“纯粹之爱”正在面临威胁与危机,甚至是濒临“灭绝”的。女性主义哲学家波伏娃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说过“真正的爱情应该建立在两个自由的人相互承认的基础上。”,顾名思义,成立的条件为“自由”和“相互承认”,也就是同为主体和相互融合。然而这个条件在如今已然很难达成。不仅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扼杀了对“他者”的承认,资本社会下的景观社会也让爱欲变成了一种单向度的景观,虚假的需要代替了真实的需要,而人们无法辨别,不得不被迫的接受这个“当下的愿望”,甚至失去了抗争和批判的能力,把这一切当做“应有之义”。在最后我们引用一下张世英老先生的“人生四境界”与开篇的四种概念相对应。先生提到第一个也就是最低的境界是“欲求的境界”,在这个境界中人只知道满足个人生存所必须的最低欲望,其与世界的关系属于“主客未分”。第二是“求实的境界”,这种境界则进入了初步的“主—客关系”,人有了自我意识,能够分清自我与他者,寻求对“外物”的进一步理解,对于同为人的他者产生了“同类感”,以及道德意识。以此要进入第三种境界——“道德的境界”,其尚属于主—客关系的结构,但此时自我以对万物一体相通的领悟作为自己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标,并为止奋斗不已,也就是具备了一种不惧生死的理性的追求精神但身处道德境界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所以仍有着主客的区别,也就是否定之否定并没有彻底完成没有达到破立扬弃之后的“融合”与新生。但道德的实现和完成,就是道德的极致,也就是道德境界的结束,便来到了第四种境界——“审美的境界”,这是一种高级别高纬度的“主客融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的超越结构,它包摄道德却又超越道德人们不再出于道德义务的强制来做某事,不再只是为了“应该”(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规训社会的代名词)而做某事,而是完全出于一种融合的自然的境界之中。这四种境界分别对应了性满足、情感、爱欲和纯粹之爱。
感觉也基本解释了为什么我对于某些恋人之间流露出的气场感到恶心,而有些则让我平静和享受,这是对于爱的审美在起作用。
看书的时候听的是玛丽亚凯莉的《Without You》和惠特尼休斯顿的《I Have Nothing》。感觉当代真的很难再找到配得上这两首歌的爱情了。
开篇第一段文字
我在这里讲的故事,换做别人可能可以写成一本书。然而,我在这“故事”里不遗余力地活过。倾尽了所有德行,所有仅仅将回忆记录下来。往事断断续续,支离破碎,但我不打算靠虚构事实连通补缀,这种修辞铺陈,会浇灭讲述的热忱,最后一丝意趣也化为乌有。
是的,在日记里撒谎的话,会被记忆之神背弃的吧,我始终抱有这种朴素的认知。
每个人心里应该都存在着一扇窄门吧,我的窄门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能够共鸣阿丽莎。她在幼时看见了母亲偷情,看见了欲望的恶,成长时心里的无助彷徨因为没办法舒缓,选择了宗教,最后又因为宗教倡导的无私奉献,让自己具有了神性,无法产生对俗世欲望的追求,想爱又不能爱。
我虽然家庭美满,但并不意味着我未曾受过类似创伤,在高中,我努力表现的像正常人,却常会受到创伤折磨。我恨人与人之间世俗意义的比较,因为我曾经认为我在这方面已经一败涂地。这道宽路于我而言已经被玷污了。于是我只能去追寻窄路。我追寻的窄路与阿丽莎却不相同。高中那会我非常喜欢听轻音乐。可以说,我完全可以接受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游戏,但我无法接受没有轻音乐的生活。有那么几首流行改编的钢琴曲(我当时不知道还有原曲,我还以为钢琴版本就是原曲呢quq),分别是,《Heal the world》, 《We are the world》和《You are not alone》,我印象非常深刻(哪怕当时我根本不去记歌名,轻音乐是这样的)。每当循环到这几首,我都会不厌其烦地享受心底的宁静。哪怕已经听过100遍,500遍,我依然会感觉我心如赤子,往事都离我远去了。有一天,我用家里电脑上的网易云搜这几首歌,想找找有没有这几首歌的hires(发烧友是这样的)版本。我爸当时看我在搜这个,惊讶地问我,你居然会听这个?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因为我爸几乎从来不会主动和我交流音乐。我当时感觉到他的目光中存在着一种不可言说的神圣。他之后把他仅有的CD随声听给我了,还有Michael的《Dangerous》CD专辑。我和我爸居然在这个地方,获得了跨越时空的共鸣,这是我目前人生中,对于“不约而同”的最佳注解。
我想找的那三首曲子,无一例外,都改编于MJ的流行乐。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感动。从此,我便很少听轻音乐了,我开始听MJ。我听到了他对于爱与欲的挣扎,我听到了他对于权贵的抗争,我听到了他对于世人的大爱。那时候的我决心,要做一个像他一样,大爱世人,为人间带来爱的使者。我努力对身边所有人都温柔。我会和尖子生一起讨论数学题,也会和学业不理想的同学谈心,谈论过去,谈论未来。我对大部分人都充满着好奇,我认为他们真的都很可爱啊,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遭受了好多生活中的,学业上的苦痛,我实在是不忍心让他们在我这里再感受到一丁点恶意了。我认为就这么活在世上,世上便多了一点光,就算得上不枉此生了。这是我自己信仰的雏形,几首歌,一位已经过世的歌手,当然还有我一直藏在心里对善的渴望,塑造了这些。
逃离窄门
我逐渐感觉到,我虽然在与我心里的神圣靠近,但我却在渐渐远离实在的人。我清楚地感受到,我与我同学之间的友谊似乎与其他同学之间的友谊不一样,没有人和我称兄道弟,没有人会和我开俗俗的笑话,他们不会对着我大笑,也不会大哭。我感觉到痛苦,因为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渴望能给其他人传递温情,但是我们的距离变得太远了。我想起了伊卡洛斯的故事,不要飞得太低,海水会沾湿你的翅膀,也不要飞得太高,阳光会融化你的翅膀。我感觉我确实离太阳太近了。
但没有给我时间去探索信仰的平衡之道,时间来到高三,我来到了上中,陌生且高压的环境,让我缩进了龟壳,我对于MJ更沉迷了。带有这种态度的我,也是没有交到朋友。我感觉正是这段时间,我开始主观地去疏远实在的人了。可能是因为同龄人真的都很厉害,我“神爱世人”的游戏到此为止了(可能是我今天写下这些,这个游戏才算是真的画上了句号)。
上大学后我开始思考别的事情,比如,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文明的兴荣,导致了无止尽的战争。没有一个人希望文明衰弱,希望战争,死亡的发生,每个人不过是各司其职,做好了各自位子上该做的事情,但事情就是发生了,难以避免。我也没有太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我感觉我会想极端。于是我想给自己设一套道德行为准则,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向这套准则靠拢,那么阶层就不会分化,矛盾也不会累计为战争。具体这个准则是什么,我已经记不大明确了。说实话我上面说的这些只是我从回望的视角总结出来的一些事情,可以解释很多时候我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我会对于某些事情生理性反感。当时的我可能只是循着模糊的感召行事。毕竟我之前也从不记录下些什么东西,还是很难考究的。
总之,我意识到我其实已经在窄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了,我已经太久没爱具体的人了。诶,爱过一位,但是我认为爱的也不甚具体,可以说正是有这份感情,才让我在读完《窄门》后有如此多纷乱的思绪吧。